
蔡元培是一位暗殺高手、恐怖分子 萬維作者: 謝選駿 2009-05-03
“五四運動”與恐怖主義
現代人一般用“五四運動”來指代“新文化運動”,而蔡元培其人又是新文化運動的幕後黑手之一,因此探討一下蔡元培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有助于發現這場運動的暴力性質。
“新文化運動”與恐怖主義的這一內在聯系,不僅被後來的歷史一再證明,而且大家都不會忘記,1966年爆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幕後黑手毛澤東,正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
“文革”的許多惡劣做法,都可以追溯到“五四”。
之一 (蔡元培的恐怖活動和偽造文書)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恐怖分子已經成為全球聲討、追剿的對象,但是有一個恐怖分子例外,那就是蔡元培(1868-1940年)。
2008年是蔡元培誕辰一百四十周年,不少人紛表紀念。這是為什麼?因為蔡元培除了是一位暗殺高手、恐怖分子,後來也成為北京大學的校長,並通過北大晉身為“民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進而變成了“新文化黨”的領袖人物,並把北京大學辦成了一個培養恐怖分子的巢穴,把新文化運動變成了一個類似于阿富汗神學生運動(塔里班)那樣的暴力運動,裹脅左右兩派卻左右逢源,一直發展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專政。如此看來,紀念蔡元培,等于是在紀念恐怖分子。
蔡元培,浙江紹興人,1885年十七歲考取秀才,1886年十八歲設館教書。1890年二十二歲中進士,1894年二十六歲授翰林院編修,堪稱天資聰慧。可惜中國在滿洲人的殖民統治下,無力對抗西方滲透和日本侵略,這迫使三十六歲蔡元培在1904年走上了恐怖主義的道路。
這年7月31日,東京留日學生、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的主持人楊篤生和團員何海樵等人在上海組織成立了“暗殺團”,決定全面推進“鼓吹、暗殺、起義”三大任務,而以“暗殺”為重頭工作。何海樵介紹蔡元培加入暗殺團。不久,章士釗、劉光漢等人也加入了暗殺團。章士釗寫信給陳獨秀讓他來上海參與暗殺工作。陳獨秀大約在10月間來到上海,就住在蔡元培安排的英租界新閘路余慶里,這里已成了暗殺團的秘密機關。陳獨秀一到上海,隨即加入了暗殺團。11月19日,暗殺團在滬行刺前廣西巡撫王之春不中,暴露了目標,黃興、張繼等十余人被捕,上海的暗殺活動也只得暫時停止。為了躲避當局的追捕,陳、蔡作鳥獸散,各自奪路逃亡。這段短暫的“共事”便告結束。
蔡元培認為︰暗殺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偽裝隱蔽的武器,他決心自制化學毒藥。要自制化學毒藥就需要有懂化學的人,他馬上將愛國女校的化學教員鐘憲暢、俞子夷吸收入團。
俞子夷配制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來一只貓,強令服了幾滴,貓即中毒而死。後來蔡元培又認為液體毒藥使用還不太方便,易被人發覺,如能改成固體粉末更好,于是急去書店買了一批藥物學、生藥學和法醫學書籍,親自領導研究。
不久,蔡元培覺得還是用炸藥更好一些,隨即轉向研究炸藥。他帶領研制小組日夜攻關,終于自制出了一種體積小、威力大的炸藥。另外,蔡元培認為女子去實行暗殺比男子更隱蔽些,因而他在愛國女校特別注重化學課的講授,以便培養暗殺種子。此後,由蔡元培研制的炸藥,不斷由暗殺團團員帶回國內,掀起了暗殺高潮,揭開了二十世紀中國的血腥一頁。
由于暗殺高手的恐怖經歷留下了精神創傷,蔡元培後來不敢再吃葷菜,因為葷菜讓他想起了血肉橫飛的人體組織。當然,冒充好漢的蔡元培是不肯承認這一點的,他詭稱自己是在赴德國萊比錫游學時,听朋友李石曾談到食肉的害處,正好他又看過俄國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著作中關于打獵的慘狀描寫,于是宣布不再食肉的。但是他其實不能自圓其說。例如他勸告朋友壽孝天說︰“蔬食有三義︰一衛生,二戒殺,三節用。”並表明自己蔬食專是因為戒殺。但壽孝天回信引用杜亞泉的話挖苦蔡元培說︰“植物未嘗無生命,戒殺義不能成立。”對此,蔡元培不得不坦白說︰“戒殺者,非倫理學問題,而感情問題。”他解釋說,“蔬食者不是絕對不殺動物,一葉一水中也有不知道多少動物,但因為常人無法看見,所以感情也未能顧及。而對于能夠看見的動物,感情則可以顧及,所以要戒殺。”
由此可見,蔡元培確實是因為自己從事所恐怖活動造成的“感情問題”而被迫吃素的。當然應當承認,這比毛澤東等人後來的“談笑用兵”還是文明得多。因為蔡元培等人只是新文化黨的野蠻化運動的始作俑者,而非集大成者和“頂峰”。其實,這些恐怖分子的終極目的並不是推翻滿清統治,而是要顛覆整個中國社會,徹底粉碎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
分別多年之後,陳獨秀、蔡元培這兩位恐怖分子都進入文化界,並再度見面,成為上下級同事,在文化領域掀起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碎一切的恐怖活動︰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1916年11月26日,陳獨秀和亞東圖書館的經理汪孟鄒等人離滬北上,28日抵京,入住前門外的中西旅館。而12月26日,北洋政府對蔡元培的任命正式下達。名為求“賢”若渴實為招降納叛、網羅恐怖主義黨徒的蔡元培听到陳獨秀來京的消息後,當天上午,即親赴陳獨秀所住的旅館,邀請陳獨秀到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上任,1月13日,經教育部批準,陳獨秀被正式任命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消息傳出,全校震動,新文化黨徒熱烈歡迎,奔走相告;但教師中的正派人士卻竊竊私議,嘖有煩言,說︰“陳獨秀生只會寫幾篇策論式的時文,並無真才實學,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夠,更不要說出任文科學長了。”但恐怖分子出身的蔡元培卻指鹿為馬地胡說︰“仲甫先生精通訓詁音韻,學有專長,過去連太炎先生也把他視為畏友,怎麼說無真才實學?”新文化黨徒們像1957年反擊右派時一樣紛紛表態支持,說陳獨秀在文字學考據方面有研究有著述。這樣眾口一詞,堵住了正派人士的嘴。
而蔡元培為聘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不惜偽造履歷文書。這一犯罪行為可不是用來推翻滿清的,而是用來對付民國制度的。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當天上午,蔡元培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館走訪陳獨秀,勸說陳獨秀到北京大學就任文科學長。汪原放當時和陳獨秀同住在旅館,他在日記中寫道︰“12月26日,早9時,蔡孑民先生來訪仲甫,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從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來看仲甫,有時來得很早,我們還沒有起來。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陳獨秀被蔡元培的誠意感動,決定舉家遷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請派文科學長。全文如下︰
敬啟者︰
頃奉函開,據前署北京大學校長胡仁源呈稱,頃據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函稱,錫祺擬于日內歸省加有他事相累,一時不克來校,懇請代為轉呈準予辭去文科學長職務等語,理合據情呈請鈞部鑒核施行等因到部。查文科學長夏錫祺既系因事不克來校,應即準予辭職,所遺文科學長一職,即希貴校遴選相當人員,開具履歷送部,以憑核派等因到校,本校亟應遴選相當人員,呈請派充以重職務,查有前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斯任,茲特開具該員履歷函送鈞部。懇祈核施行為荷。此致教育部
北京大學
中華民國六年一月附履歷一份︰
陳獨秀,安徽懷寧縣人,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以上引自《北京大學史料》,第2卷,第326-327頁)
這份公函1月11日發出,13日範源廉就簽發“教育部令”第三號︰“茲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此令。”15日,北京大學張貼第三號《布告》,布告陳獨秀任文科學長。五天之內,蔡元培為陳獨秀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走完了全部的法定程序,“效率”極高。而在貼出《布告》的同一天,陳獨秀正式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蔡元培急急忙忙辦理陳獨秀的任職手續,就是因為做賊心虛,怕教育部發現他偽造履歷文書的犯罪行徑、拒絕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因為公函中所附的陳獨秀“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的履歷,均是蔡元培一手編造的。
陳獨秀根本就不曾畢業于什麼日本大學。陳獨秀一生五次東渡日本,每次在日本的逗留時間都不長,沒有接受過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學的學歷教育,更沒有所謂“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的資格。另外,陳獨秀沒有擔任過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等職。陳獨秀也承認自己沒有“學位頭餃”,“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蔡元培之所以要拿這麼一份偽造的履歷遞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保證陳獨秀順利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而陳獨秀在接受蔡元培聘請的同時,恐怖分子陳獨秀還向蔡元培極力推薦那位沒有拿到博士學位卻冒充到處美國博士的胡適,蔡元培也欣然應允,聘請二十七歲的假博士胡適為北大教授。結果把北京大學弄得烏煙瘴氣。
1917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吹響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語言暴力的殺戮號角。在緊接著的第二卷第六號上,陳獨秀發表了更為激進的《文學革命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血腥氣息開始彌漫開來,注定要未來一個世紀的中國帶來一場滅頂之災。對于蔡元培與陳獨秀在北大的這段文化破壞工作,同樣被蔡元培“破格”弄到北大、成為講師的梁漱溟後來自吹自擂地粉飾說︰“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陳獨秀先生是佼佼者。當時他是一員闖將。影響最大,也是最能打開局面的人。但是陳這個人平時言行不檢,講話不講方式,直來直去,很不客氣,經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討厭他,校內外都有反對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歡他、愛護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個。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維護和支持,以陳之所短,他很難在北大站住腳,而無用武之地。”這真是惺惺惜惺惺,猴子愛猴子。
在號稱“五四運動”的文化破壞中,陳獨秀不僅是蔡元培手下的前敵總指揮,而且身先士卒,沖鋒陷陣。1919年6月8日,陳獨秀與李大釗商量後,親自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又和鄧初、高一涵到宣武門外的“新世紀游藝場”散發,當場被捕。後經蔡元培等後援人士解救,于9月16日獲釋。之後又因為在甦聯指揮下建立恐怖組織“共產國際中國支部”遭到當局追緝,于1921年10月4日在上海漁陽里二號陳宅樓被捕。蔡元培和胡適“博士”給上海的法領事發電報,請他們釋放陳獨秀。最後,法官宣布將陳獨秀等人先放出來,但是七天之後需到堂听會審結果。10月26日,法領事當堂宣布判罪罰一百大洋了案。由此可見,法國等西方國家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縱容和支持。
1922年8月9日上午,總巡捕房特別機關探目長西德納,督察員黃金榮等包圍上海法租界環龍路銘德里二號,逮捕陳獨秀,罪名是“藏有違禁書籍”。8月14日,陳獨秀從拘留所的獄卒處知道在《時事新報》上有一條消息︰“蔡元培質問法國大使,長辛店工會發營救陳獨秀電報。”最後,法院判罰陳獨秀四百元,由保人保出,所抄書籍一律銷毀。這比後來共產黨專政期間“收藏反動書籍”的處罰輕微得多。但共產黨壓制言論自由的做法,顯然來自西方殖民國家的傳授。事實上,反清、反專制、反西方、反壓迫的自由思想家鄒容(1885-1905年),早在這之前就被西方國家關押迫害致死。
1932年10月15日,由于中共黨內同志的出賣,陳獨秀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十一號宅中被捕。10月19日,陳獨秀被押往南京。這一次被捕與前三次不同,被捕之後被立即引渡給國民政府,將依據所謂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起訴。在北京大學任文學院院長的胡適給蔡元培拍了一份電報,請求營救他的推薦人︰“請就近營救陳獨秀”。
蔡元培此時已由南京到上海。1931年10月下旬,蔡元培、楊杏佛、林語堂等人聚在上海法租界亞樂培路三三一號(今陝西南路一四七號)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國際交換處,商議如何營救陳獨秀。蔡元培對楊杏佛說︰“我看速擬一快電致南京國民政府,同時將電文交《申報》發表。”並建議“仲甫是文化中人,宜多幾個人聯名致電,同時要致電中央黨部,目前此案由他們經手,對陳獨秀很不利。”最後在電文上署名的有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潘光旦、董任堅、全增嘏、朱少屏等為新文化黨徒。以快郵代電寄往南京。在蔡元培等人多方營救下,蔣介石官送私情,饒了陳獨秀一命,將陳案交江寧地方法院審理。
1940年3月5日,七十四歲的蔡元培在香港養和醫院逝世。六十多年後,張耀杰《新文化運動的路線圖》一書提出了一個“蔡元培悖論”︰新文化運動的一批“新青年”中堅,說到底,都是蔡元培帳下的“新文化黨”,但最終又都一個個叛離蔡元培的“兼容並包”論︰陳獨秀、魯迅的激進不必說,即便晚年覺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適,也離蔡元培“兼容並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遠。該書序言說︰“長期以來,我們幾乎是一面倒地歌頌新文化運動的偉大功績,與此同時,我們可能忽略了它的一個致命的隱患︰不寬容。這種不寬容體現在胡適的同道身上,有時候也會體現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適身上。”“由《新青年》雜志開啟的新文化運動的路線圖由胡適而陳獨秀而錢玄同、劉半農,就是從‘平等討論’到‘不容匡正’到罵人有理。這條‘不寬容’的邏輯一路下行,必然付諸‘不寬容’的行動。”
有人驚嘆︰誰也沒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黨”的實際結果,卻使中國社會出現了長達一個世紀的不寬容的“主旋律”。這似乎表明“蔡元培悖論”的悲劇——“兼容並包”之共生種子,並不一定能結出“兼容並包”之共生果。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批“新青年”中堅,說到底,都是蔡元培帳下的“新文化黨”,但最終又都一個個叛離蔡元培的“兼容並包”論︰陳獨秀、魯迅的激進不必說,即便晚年覺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適,也離蔡元培“兼容並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遠。“誰也沒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黨’的實際結果,卻使中國社會出現了長達一個世紀的不寬容的‘主旋律’。”﹝朱健國《“蔡元培悖論”與新文化運動路線圖》﹞論者指出,所謂“新文化運動”的致命隱患就是不寬容。論者稱此為“蔡元培悖論的悲劇”,並說“‘兼容並包’思想為何不可傳遞不可再生?蔡元培可能始料未及。”
其實,根據我們對蔡元培的論述不難理解,“蔡元培悖論”就是蔡元培自己一手導致的。因此根本不存在“蔡元培悖論的悲劇”,而只有“蔡元培悖論的鬧劇和丑劇”。蔡元培這個風派頭子,兼有前清進士、光復會組織者、同盟會參與者、首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兩度“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的混雜閱歷,不論他多麼善于偽裝“兼容並包”,他的假包裝終于在“打倒孔家店”的問題上破了局。因為不論新文化黨的說辭如何,從它後來表現看,就是企圖在“不破不立”的鬧劇和丑劇中,取孔家店而代之。其極端表現,就是林彪在毛澤東授意下,企圖用《毛語錄》取代《論語》,修齊治平一番。可惜毛語錄質量太差,用了不到十二年就破損不堪了,還不如希特勒《我的奮斗》。
用“一娘養九子,九子九個樣”,來描寫蔡元培這個新文化黨的黨魁和新文化黨的黨徒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傅斯年、羅家倫等人的關系,並不確切。因為蔡元培這個一娘和他的九子實在是一個模子里澆出來的造反派,這個一娘九子的造反亂倫的結果,就促成了後來居上的毛澤東及其鬧劇文革,把毛的新文化黨的祖師爺們也一起否定了。
而蔡元培偽造履歷文書的罪行,後來也被毛澤東等人有系統地繼承發揚,用來批量篡改歷史記載,並堂而皇之地叫做“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不僅黨史,而且國史,全部重新偽造一遍。這樣的歷史,還不應該結束嗎?
毛澤東與蔡元培,還有另一層私下的關系。毛在湖南師範中專讀書時,用過《倫理學原理》的課本,就是蔡從日文翻譯的,這本書對毛發生過很大影響。1918年春,毛到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小職員,就直接認識大人物蔡元培了。1920年10月,湖南教育學會舉辦“學術講演會”,邀請蔡元培、章炳麟、吳敬恆、張東蓀,以及杜威、羅素等人去湖南講演。小嘍羅毛澤東曾為湖南《大公報》擔任講演的記錄。蔡元培一共講了十二次之多,其中有兩篇就是毛澤東記錄的,在報上刊登時署名︰“蔡孑民講,毛澤東記。”看來毛很是引以為榮。一篇叫作《對于學生的希望》,一篇叫作《美術的價值》。
從來沒有上過大學的毛澤東後來異想天開,“創辦自修大學”,而這位蔡元培竟也“極力支持”,並應聘為“名譽校董”。收到《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後,還“歡喜得了不得”,甚至寫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學的介紹與說明》的長文,發表于《新教育》第五卷第一期上,簡直是斯文掃地。可見根本不用等到1966年的文革,這批“新文化文黨徒”已經胡作非為到何種地步。後來文革毛的“五七干校”之先河,實在是蔡元培“極力支持”的結果。難怪1962年春大饑荒時期,蔡元培的兒子蔡無忌在北京參加一次酒肉招待會時,陳毅特地領他去見毛澤東,毛澤東熱情地握著蔡無忌的手說︰“你的父親真是好人。”
蔡元培這個文化五蠹,終于有了毛這樣一個文化殺手。毛說蔡是“好人”,真是惺惺惜惺惺,猴子愛猴子。
“五四運動”與恐怖主義,其理昭昭!
2009年5月4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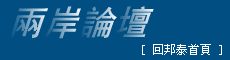
 註冊
註冊
 搜索
搜索
 風格
風格
 論壇狀態
論壇狀態
 論壇展區
論壇展區
 我能做什麼
我能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