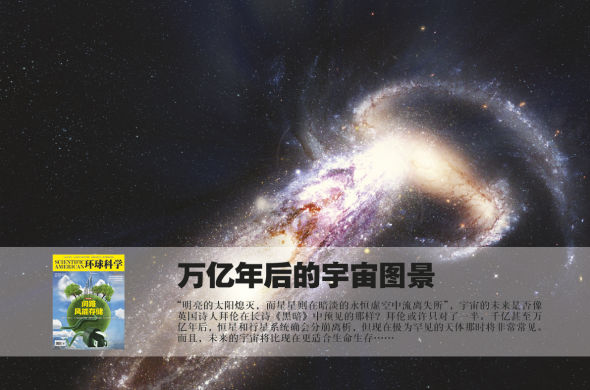揭秘万亿年后宇宙图景:将更适合生命生存
恒星和行星系统将分崩离析;现在极为罕见的天体到了未来将非常常见,而且未来的宇宙将比现在更适合生命生存……数千亿年后,宇宙将会变成这样吗?
时间那不可阻挡的脚步,总能激起我们对宇宙遥远未来的思考。但思考的结果通常令人沮丧。50亿年后,太阳会膨胀成一颗红巨星,在缓慢变暗前会吞没内太阳系。但这仅仅是整个未来的一个瞬间的画面——实际上,无穷短。随着天文学家放眼未来,例如幽默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在《宇宙终点的餐馆》中所写道的“5 760亿年”,他们会看到一个充满了无数正在暗去的天体的宇宙。到那时,空间的加速膨胀会把已经位于我们银河系之外的每一样东西都带到我们的视线之外,留下一个更加空荡的夜空。在1816年的长诗《黑暗》中,拜伦勋爵预见到了这一前景:“明亮的太阳熄灭,而星星则在暗淡的永恒虚空中流离失所。”
但好消息是:黑暗的降临只是故事的一半。恒星形成这个宇宙现象,确实在很久之前就已过了它最光辉的时期,但宇宙并没死去。奇异的新物种将会进入天文学家的动物园。当前罕见的怪异现象(如果有的话)将会司空见惯。宇宙中适宜生命生存的环境,甚至会变得更多。
科学的“末世学”——对极遥远未来的研究——在宇宙学和物理学中具有卓越的历史。这类研究不仅让人着迷,也为检验新理论提供了一个概念上的平台,让一些抽象理论可以变得更为具体——当宇宙学家描述空间形状对宇宙命运的影响时,这个宇宙学上最为抽象的概念也许就更容易理解一些。试图调和关于基本粒子与作用力的不同理论的物理学家预言,只有在数万亿年甚至更久之后,诸如质子衰变和黑洞蒸发的现象才会发生。越来越多天体物理学家也在他们的有关恒星和星系演化的模型中,引入了极为遥远的未来。过去十年里,他们试图再现自大爆炸以来,恒星和星系的形成及其成分变化的方式。随着科学家对过去的认识不断加深,他们可以推测出在遥远的未来,宇宙会发生什么。
恒星的未来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的恒星形成专家格雷格•劳克林(Greg Laughlin)是研究上述问题的先驱。在读研究生时,他就编写了一个计算机程序,来计算极低质量恒星的演化,但忘记了在达到宇宙目前的年龄之后,让程序停止运算。就这样,这个程序不停地运行,得出了对未来数万亿年的预言——尽管这个预言存在很多错误,但足以让他迷上了这个研究课题。
为了了解恒星的未来,我们需要知道它们是如何形成的。恒星诞生在气体和尘埃云中,这些星云的质量从几十万到数百万个太阳质量不等。这些遍布在银河系中的“恒星育婴室”已诞生了约几千亿颗恒星,最终还会形成数百亿颗。然而,这些业已“出生”的恒星透支了未来:新一代恒星的原始物质正在被耗尽。就算大质量恒星以超新星爆发死亡的形式,向星际空间返还一些物质;就算星系还可以从星系际空间吸积新鲜气体,这些新的物质仍无法重新补足被恒星锁住的物质。目前,银河系中,星际气体的总质量只有恒星的十分之一左右。
今天,银河系中恒星的形成速度接近每年一个太阳质量,但在80亿到100亿年前的鼎盛时期,这一速率至少是目前的10倍。劳克林估计,时间尺度每向前延伸10倍,恒星形成速率就会降低到原来的十分之一。因此在一千亿年后,恒星形成速率会降低到目前的十分之一,而在一万亿年后,这一速率则会降低到眼下的百分之一。
不过,剧烈的变化可能会打乱恒星形成速率不断降低的稳定进程。例如在不久后——“不久”指的是几十亿年后,我们所在的银河系必然会面对汹涌而来的仙女星系,它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巨型旋涡星系。这两个星系的致密核心区要么会发生碰撞,要么会绕着它们的公共质心转动。这一相互作用会形成“银河仙女星系”。通过搅拌星际气体和尘埃,银河仙女星系会暂时激活恒星形成过程,引发天文学家称之为的“星暴”。一旦这一生长势头过去,这个并合后的系统就会极为类似一个椭圆星系,即一个恒星形成所需物质稀少、恒星形成速率很低的成熟系统。
除了形成数量会减少之外,未来的恒星会显示出它们对原始物质的改变作用。大爆炸的高温熔炉锻造出了氢、氦和锂,而所有更重的元素都是由恒星创造的,尤其是在它们的生命晚期——要么是随着年龄增大会抛射外层物质的红巨星,要么是超新星爆发。红巨星提供了绝大部分较轻且丰度较高的重元素,例如碳、氮和氧,而超新星所能产生的元素则更多,包括铀都是由超新星产生的。所有这些元素都会混入星际气体中已有的元素里,使得下几代的恒星在诞生时就拥有了更多的物质。太阳,这颗年龄为50亿年的、相对年轻的恒星,所拥有的重元素数量是100亿年前形成的恒星的100倍。事实上,一些最老的恒星几乎不含有任何重元素。未来的恒星甚至会含有更多的重元素,这会改变它们内部的运转方式和外观。
生命的新居
新生恒星中,重元素的稳步增加会导致两个显著效应。第一,这会增大恒星外层的不透明度。氢和氦几乎都是透明的,但即便是为数不多的重元素也会吸收辐射,降低恒星的光度。恒星内部的力平衡随之就会偏移,因为较低的光度意味着恒星会以更低的速率来消耗核燃料。如果只有这一效应在起作用,那么一颗富含重元素的恒星会比一颗相同质量、但缺少这些元素的恒星活得更久。然而,第二个效应会抵消作用:重元素是核聚变的负担。因为它们不参与核聚变,因此在特定质量的恒星中,重要元素的存在会阻碍恒星获得核燃料,进而缩短恒星的寿命。
劳克林和他的同事、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弗雷德•亚当斯(Fred Adams)在1997年最先对这两个效应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第一个效应会在未来的数万亿年内起主导作用:在新生恒星中,由于重元素增多,恒星的不透明度升高,进而寿命延长。然而,重元素最终会成为恒星的重要成分,占据相当的比例,然后开始始缩短恒星的寿命。这两个效应的交叉点,就是新生恒星中重元素的比例达到目前值的4倍时。
重元素还有利于行星与恒星一起形成,因而为生命的出现提供了不错的前景。天文学家已经测量了一些恒星的元素丰度,这些恒星周围有700多颗太阳系外类木行星。他们的结果显示,拥有较多重元素的恒星更有可能拥有一颗或多颗巨行星。“这一现象说明,行星的形成和重元素数量之间存在明确的相关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行星搜寻专家约翰•约翰逊(John Johnson)说,“因为星际介质中重元素不断增多,行星出现的概率就可能上升。”
那类地行星又会怎样?虽然空间望远镜才刚刚开始提供有关类地行星的这类数据,但它们的形成应该也和宿主恒星的重元素丰度相关。这一相关性甚至会更强,因为类地行星几乎全由较重的元素构成。简言之,极为遥远的宇宙应该会充满了行星。尽管恒星的形成速率会变小,但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行星还未诞生。
最开始,行星的增多似乎生命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极遥远的未来,绝大多数恒星都比太阳小得多,也暗得多。幸运的是,即便是一颗低质量、暗弱的恒星,也能衍生生命。光度仅有太阳千分之一的恒星,就可使距其很近的行星具有合适的温度,维持液体存在所需的温度,满足生命存在所需的可能条件。
行星不应该只是变得更为普遍,还会含有更多生命所需的物质。除了液态水,地球上的生命以及科学家猜想的几乎所有生命形式还会依赖碳、氮和氧。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元素相对丰度的提高应该会形成更多适宜生命存在的行星。因此,随着恒星形成逐步减缓,每一颗新生的恒星拥有一颗或多颗可承载生命的行星的概率应该会逐渐提高。一些新生恒星的质量可能很小,光度可能很低,这使得它们可以持续然绕数千亿或者数万亿年(这并不是说如此长寿的恒星才是生命的起源与演化所必需的条件)。然而,无论今天的宇宙是充满了还是鲜有生命,未来它应该都会拥有更丰富和更多样的生命形式。
当行星碰撞时
行星系统的寿命是如此之长,于是新的效应就会显现出来。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太阳系是稳定的;没有人担心地球的轨道很快会日渐混沌,使得我们和金星相撞。当我们探究几十亿年的时间尺度时,这种确定性就会消失。2009年,法国巴黎天文台的雅克•拉斯卡尔(Jacques Lasker)和米卡埃尔•加斯蒂诺(Mickael Gastineau)对太阳系四颗内行星的未来轨道做了数千次模拟,在每一次的模拟中,他们都会稍微改变这些行星的初始位置(相对上一次)——只有几米的偏离。结果发现,在未来的50亿年里,水星有大约1%的概率会猛烈撞上金星,为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可能会牵涉到地球的碰撞埋下了伏笔。在未来1万亿年间,这样的碰撞发生的可能性很高。
当仙女星系和银河系并合时,这个潜在的碰撞进程就会被打乱,因为它会重构这两个星系的引力场,使太阳系发生大规模重建。正如劳克林在评论拉斯卡尔和加斯蒂诺的结果时所说:“我们现在要弄清楚的是,能如此轻易影响到太阳系的动力学混沌(发生在确定性系统中的貌似随机的不规则运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掌控银河系中的行星。”
在一颗恒星的行星系统中,轨道混沌也会发生在大得多的尺度上。在紧密结合的双星、三合星以及成员更多的聚星系统中,恒星会在相互引力的作用下绕着每个系统的质心运动。对于星团乃至整个星系而言也是如此。在所有这些结构中,恒星几乎永远都不会相撞——虽然在天文学上它们若比邻,但空间的巨大膨胀会让它们相隔天涯。
然而,在长时间下,“几乎永远都不”会演变成“有时”,最终变成“几乎总是”。每个双星系统最终会在外部引力的作用下瓦解,或由于引力辐射带走系统的能量,而逐渐靠拢进、并合。如果两颗恒星相距较远,双星系统会面对前一种情况;相反,则会遭遇后者。
当两颗恒星并合的时候,它们暂时会形成一颗质量更大也更亮的恒星。即便是一颗木星这样大的行星也会造成类似的效应,不过是在较小的尺度上。设想一颗质量只有太阳十分之一,寿命接近一万亿年的中等恒星,并假设它有一颗类木行星。 如果这颗行星的轨道运行周期不止几天,那它最终可能会被甩出这个系统。反过来,如果它在更靠近该恒星的轨道上,最后就有可能会和恒星并合,为恒星提供新鲜的氢补给,在短时间内猛烈地提高该恒星的能量输出,产生类似新星的爆发。未来,这样的恒星爆发会不时打断恒星数量和亮度缓慢下降的趋势。就算是一万亿年之后的天文学家也会观测到,在他们的星系里,数目不断减少的恒星中会有一些奇怪的事件发生。
恒星的宿命
甚至在数百亿或数千亿年后,甚至当恒星形成都成了“涓涓细流”,仍会有大量恒星继续发光。宇宙中绝大数恒星都有着低质量和极长的预期寿命。恒星的寿命和它们的质量成显著反比——大质量恒星十分明亮,它们会快速燃烧,在几百万年后爆炸;质量远小于太阳的恒星则可持续存活数千亿年甚至更长。这些恒星会非常缓慢地消耗自身的燃料,以致于在极为漫长的时间跨度里,即便物质有限,也能为核燃烧提供原料。
不同质量的恒星会以不同的方式死去。太阳会变成一颗红巨星,而随着外层物质全部消散,进入星际空间,它的核心会成为一颗白矮星——一个几乎全由碳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地球大小的致密恒星遗迹。但在质量不足太阳一半的恒星中,它们的核心温度永远也无法触发那种能使恒星进入红巨星阶段的核聚变反应。天文学家认为,这些恒星最终会演化成氦白矮星——正如其名,这种恒星差不多全部由氦组成,只有少量的氢和微量的其他元素。在今天的宇宙中,当两颗距离很近的双星剥离掉彼此的外层物质,且在其氦核被点燃之前,偶尔也会形成氦白矮星。但天文学家还未曾发现通过恒星演化的正常过程而形成的任何氦白矮星,因为自大爆炸以来,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样的过程。也许要在很多年后,我们的那些后来能看见那些孤立的氦白矮星。
质量更大的恒星则会经历更为剧烈的死亡。大质量恒星的核心会坍缩成一颗中子星或黑洞,该过程产生的激波会使得恒星的外层以超新星的形式爆炸。随着大质量恒星的消失,今天不断出现在宇宙中的这些爆炸也会销声匿迹。不过,另一种超新星仍会偶尔点亮天空。被称为Ia型超新星的这类爆发,产生于有一颗子星是白矮星的双星系统。按照最受天文学家青睐的模型,来自伴星的、富含氢的物质会在这颗白矮星的表面累积,直到突然的核聚变产生超新星。在未来的1 000亿年里,只要存在质量足够大的伴星,这样的事件就会发生。
在另一个超新星模型中,两颗白矮星会极为靠近地绕着它们的公共质心旋转。在此过程中,它们的轨道运动会导致该双星系统发射出引力波。这一辐射会带走系统的能量,使得白矮星的轨道发生收缩。这两颗白矮星彼此接近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直到死亡的旋涡让它们合并,引发短暂的爆发。这些事件可能还会此后数万亿年里继续发生。
比超新星爆炸更为明亮的是伽马射线暴。这些剧烈的爆炸可以分为两大类,它们也源自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爆发持续时间在2秒以上的长时间伽马射线暴,可能是大质量恒星的核心坍缩成中子星时产生的;持续时间不足2秒的短时间伽马射线暴,则被认为源自一颗中子星和另一颗中子星或黑洞的并合。随着大质量恒星停止形成,在未来的十亿年里,长时间伽马射线暴会变得极其罕见,但短时间伽马射线暴可能仍会在未来的数万亿年里打破天空的宁静。
万亿年后
当我们用万亿年而不是十亿年来度量宇宙时间时,我们会进入一个恒星形成将会终止的时期。除了质量最小的恒星之外,所有的恒星会将燃烧殆尽,或以爆炸、或以凋零成白矮星的方式结束它们的生命。如果不考虑谜一样的暗物质,我们的银河系——以及宇宙中其他所有的星系——此时都将以黑洞、中子星、白矮星和极端暗弱的红矮星为主。红矮星非常暗弱,即便位于目前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处,不使用望远镜也无法看到它们。多令人伤心、多无趣啊。
然而,在这些已经死亡或者正在暗去的天体中,大自然仍会偶尔地产生一次猛烈的爆发,也算是对曾经照亮天空的数十亿颗恒星的短暂回忆。如果幸存下来的恒星的附近拥有行星——我们可以预期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会有,那么液态水和不同的生命形式可能就会出现,并在上面存活。如果能躲开近距超新星或者是伽马射线暴的侵袭,任何能在这些行星上起源的生命,都有可能会延续至我们无法想象的时期。
对极遥远未来的这一研究留下了一个重大且不确定的议题。高度先进的文明,如果他们存在并能持续下去的话,是否能改变宇宙的历史进程?30多年前,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对此进行了思考。作为这类宇宙猜想的主要提出者,他说:“我认为我已经证明,有充足的科学原因能让我们认真地审视如下的可能性,即生命和智慧可以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塑造这个宇宙。”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即在大爆炸之后不到140亿年时,还没有证据表明生物能在大尺度上影响宇宙。但是,时间的列车才刚刚出发。未来,生命的存在将会占用更多的宇宙资源,整个宇宙都会成为我们的花园。
在宇宙时间的尺度上,我们的存在时间或许连瞬间都算不上,几乎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未来的宇宙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可以奔向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时间段。正如奥登(W. H. Auden,美籍英国诗人)在他1957年的诗中,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所有恒星行将消失或死亡,我应该学会看向空荡的天空,去感受黑暗的壮丽,尽管这会花一点时间。”
本文作者
唐纳德•戈德史密斯可能是唯一一个曾经当过税务律师的天文学家,他的律师生涯赚了不少钱,不过很短暂。1969年,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天文学博士学位,并成了卡尔•萨根(Carl Sagan)《宇宙》系列剧的顾问。他还是其他一些节目的主要作者,例如和莉莉•汤姆林(Lily Tomlin)一起合作的《新星》剧集《哪儿有人吗?》以及系列剧《天文学家》。
本文译者
谢懿在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获天文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物理与天文学系任访问学者,目前任职于南京大学。
| |
| |
摄影师镜头下的神秘“黑衣人”白宫保镖(高清组图)文章来源: 环球网 于 作为一名白宫摄影师,克里斯托弗•莫里斯(Christopher Morris)时不时的将镜头转向白宫政要身边的神秘人群,并给他们起了一个神秘莫测的名字“黑衣人”。他们就像是从天而降的复仇者,身着黑色西装,面无表情,纹丝不动的站在各种地方—车库、飞机场、荒郊野草……
张春桥倒台前物色女秘书 称“太寂寞要个伴”(图)文章来源: 书摘 于
核心提示:张春桥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煳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作者:叶永烈,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张春桥在覆灭前夕,频繁地通过萧木发出对上海的指示。 1980年9月10日,张春桥的机要秘书严忠实在“证言”中这样写道: 我叫严忠实,1971年以前在中办机要局工作,1971年12月至1976年10月6日由组织指派张春桥的机要秘书。现在中办机要局工作。 1976年9月10日晚,张春桥让我打电话找萧木(王洪文处工作人员)到钓鱼台住,大约谈了三个来钟头。1976年9月27日晚饭后,萧木打电话给我,说他要回上海,问张春桥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我当即报告张春桥。张对我说:“叫萧木来吧。”我下楼后,又给萧去电话,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萧木到张春桥住处(钓鱼台九号楼)办公室,一直谈到十一点多钟,后回王洪文处。 两次谈话(我)均不在场,谈话内容我不清楚。 1976年12月14日,被隔离审查中的王知常作了如下揭发交待: “四人帮”覆灭前,我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之一。1976年9月23日,萧木派机要员从北京送来一封密信,信中写的主要是张春桥9月18日晚同他谈话的内容。因原件已被烧毁,现根据当时的笔记和回忆,恢复原状如下: 朱、王、王、陈、顾、章: 9月18日晚,春桥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我对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春桥同志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春桥同志又说:毛主席的身体是被邓小平搞坏的。邓小平欺骗主席,大搞翻案,被主席察觉,只好带病领导和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硬是把身体累垮了。光凭这一点,邓小平的罪也就够重的了。 二、我劝春桥同志要为人民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春桥同志说:毛主席逝世,我心中难受得受不了,胸中时常感到气闷,守灵时用手摸了一下胸口,啊呀!谁知被电视台的记者拍摄进镜头里了,引起好多人的不安。第二天,我看见春桥同志在院子里散步了。 三、我对春桥同志表示担心目前的形势,特别是军队不在这边。春桥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能同马克思逝世时比,也比列宁逝世时的形势好得多,当年托洛茨基是红军总司令,威信比斯大林高得多。邓小平虽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在于谁挂帅。目前资产阶级的力量还没有集结起来,缺少挂帅的人物。 四、我问春桥同志:中央今后会出现怎样的局面?春桥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只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如果今后要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在中央,在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吸取苏联的教训,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苏联现在变修了,将来还是会出列宁的。中国即使修正主义上台,将来也还会出列宁。 五、我讲到主席逝世后,外地有些坏人关门饮酒,引起群众气愤,上门惩罚。春桥同志说:我倒担心这方面搞得太过分了,当然群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人民是好的。有这样好的八亿人民,一定会涌现出自己的领袖。目前最困难的就是现在这一段时期,只要把这一段时期度过去就好了。现在要出邓小平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人民一定会起来反对的。 六、我对春桥同志说:广大群众普遍希望能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春桥同志说:毛选五卷的书稿已被胡乔木搞得面目全非,目前要出有困难。还是考虑出单篇,一篇一篇出的好。国庆前争取选出毛主席论接班人五条标准的。 七、春桥同志对我说:主席逝世时,苏修也发来唁电。这样大的事外交部也不请示报告,竟然收下了,最后是我从外电消息中发现了这一情况,才让他们把苏修的唁电退了回去。 八、我谈到现在人们普遍对形势感到担心。春桥同志说:要树立信心,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这是大方向。你转告上海的同志们,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准备斗争。 此信阅后即毁,不然,小人苦哉,大人苦哉! 萧木 1976年9月18日夜 几点说明: 一、朱、王、王、陈、顾、章:朱永嘉、王知常、王绍玺、陈冀德、顾澄海、章树焜。这六个人都看了此信。徐景贤也看了,是朱永嘉给他送去的。章树焜是最后一个看的,他看后我就将此信烧毁了。 二、此信的要害是第三点和第六点。这暴露了“四人帮”想通过抱成一团控制中央,来篡党夺权。同时,他们想在毛主席逝世后的这段时间里,加快篡党夺权活动的步伐,还企图利用出《毛选》五卷单篇来配合他们进行这一阴谋活动。 三、章树焜在看信时将原文抄录在笔记本上。这次我说要到北京揭发“四人帮”的罪行,章树焜将笔记本上的抄页撕下来交我。所以,萧木来信的恢复件是准确的。 王知常 1976年12月14日 在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还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居然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煳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煳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 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可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而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徐景贤毕竟头脑灵活,派人在上海医学院物色对象,借口是给“中央首长”挑选一名贴身护士。 “对象”总算找到了。照片、档案送往北京,张春桥也满意了。 就在这个护士打算动身去北京的前几天,任凭徐景贤一次次给张春桥挂电话,一直没有人接电话。 后来,1978年7月24日,徐景贤在证词中这样说: 过了几天,就是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到上海,向市委直接传话,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认为这是张春桥听了我9月21日的当面汇报后,经过进一步思考,给我们作出的交底的指令。 张春桥给我们指出:有人要搞“四人帮”,要搞上海,这样的时候,大考验就到来了。 张春桥在这里向我们发出了要打仗的动员令。萧木从北京到上海,一下飞机就直接从机场赶到康平路市委常委学习室。把在家的六名市委常委全找来,详细传达了张春桥9月27日晚同他的谈话。当时,我把张春桥的这些指令在笔记本上作了记录。到了75年10月8日,当我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时,我就认为张春桥的预言应验了,大考验的时刻到来了。 我们根据张春桥9月27日关于要打仗的指令,在上海策划了反革命武装叛乱……(注:青野、方雷:《邓小平在1976》下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发出通知,1976年10月6日晚八时,说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 当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步入怀仁堂,等待着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 坐镇现场指挥的,是叶剑英、华国锋和汪东兴。 江青在中南海就擒时,狂喊乱叫了一番,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 毛泽东去世之后,张春桥对形势分析了一番,托萧木向上海传话:“毛主席去世了,要有像毛主席那样有威望的领袖是不可能了……现在比列宁去世时好,那时斯大林威信不高,托洛茨基做过红军总司令,威望比斯大林高……” 张春桥的话,需要“翻译”方能明白:他,自比斯大林,而把华国锋比做托洛茨基。他以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因此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 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基地”。在徐景贤的笔记本上,亲笔记下了1976年9月28日张春桥派萧木传达的口信: 阶级斗争形势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到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现在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上海的工作,转告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我们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张春桥的这段话,同样需要“翻译”。他警告徐景贤,上海正面临着“大考验”,“要打仗”。 在10月初,在张春桥亲笔写下的提纲中,有着这样的句子:“革命与专政。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上海在准备着“打仗”、“杀人”。 箭在弦,弹上膛,剑出鞘。 风闻,10月7、8、9日,北京将有“特大喜讯”。王洪文一口气拍了一百多张照片,以供登台时用。上海的红纸头被抢购一空,准备庆贺“大喜之日”。 毛泽东在病重之际,曾说过:“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之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腥风血雨”? 10月6日晚,不费一弹、不开一枪,“狄克”和他的伙伴,“和平”地进入了监牢。 四月七日清晨,友人打来电话,说“方励之去世了”。我“啊”的一声,随即追问:“什么时候?”“什么毛病?”友人说:“急于向你报信,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我立即给李淑娴打电话,不通。上网搜索,得知:四月六日早上,方励之正准备去上课,咳嗽一声,就倒在椅子上,再也没有站起来。老方,你走得太突然、太离奇了! 励之给人的印象,脸色红润,嗓音洪亮,身体健壮。“六四”以后,中国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描绘方励之的特征是“走路抬头挺胸,步伐较快”。十足是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上帝的召唤,点错名了吧? 苦了李淑娴。前几年,他们家老二方哲因车祸不幸身亡。淑娴接连失去两位亲人,可以想见,痛何如之!我给她发了一个邮件,悼念励之。我还说:“你们家老二出事后,励之在回我的邮件中说:‘请相信,我们是坚强的。’现在轮到你一个人再说一遍了。”她表示,她一定要像励之那样坚强,不管多么艰难。愿淑娴节哀,渐渐走出悲伤的幽谷,平静地面对现实。 五行山,压不住 方励之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里翻滚,数日不得安宁。 我和方励之是北大五十年代的校友。我虽然比他年长四岁,由于上大学比较晚,我读历史系一年级的时候,他已是物理系四年级。他在学生时代就有点名气,名气来自他的独立特行的风格。北大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团员代表大会。主持会议的是团委书记胡启立。历来,通过报告的时候,主持人问:“大家有没有意见?”总是没有意见,照例一致通过。这次,却有一个人从老远的地方咚咚咚地跑上主席台,全场向他行注目礼。他提了一通意见,主要之点是:“究竟要把我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培养“螺丝钉”的年代,方励之的言论是惊世骇俗的。会议冷场。大家都在打听,这个人是谁?他就是物理系的方励之。 像他这样另类的人,一九五七年是很难过关的。他的同伴李淑娴、倪皖蓀在北大被打成右派。方励之是“同案犯”,所幸此时他已离开反右风暴的中心北大,到了近代物理研究所。虽然没有戴上右派帽子,还是被开除党籍,经批判后下放到河北赞皇县劳动改造。在舆论中,他是“有问题的人”,这就成了无形的帽子。右派还可以摘帽,无形的帽子却是摘不了的帽子。 六、七十年代,我们两家都住在北大朗润园10公寓,是邻居。我见到他的时候,老是心事重重,满怀愁绪。直到八十年代,我已被贬到南京,他到处演讲,造成轰动效应。我为他叫好,对人说,压在五行山下的方励之终于冲出来了,这才是他的本色。 冲天一鸣天下闻 八十年代,方励之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他的出现,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潮流席卷中国。一九八〇年,波兰发生了团结工会事件。邓小平认为,团结工会的背后是一批自由化的知识分子。这一年十二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反自由化,形势逆转。一九八一年以后,进入反自由化的周期,打出强权探照灯,搜索自由化分子。反自由化就是反思想解放。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被胡耀邦称之为“闯将”的一批人物,纷纷中箭落马,调动工作、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发配外地等等不一而足。 “江山代有才人出”。正当邓小平对文艺界、理论界施行高压之际,不料科学界冒出一个方励之。方励之独力抗拒反自由化,发出自由的呐喊。自由化和反自由化互相拉锯,魔高道高,不断攀升,终于爆发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方励之是天安门一代的启蒙导师。他的历史作用在于:接过思想解放运动的火炬,点燃民主运动的圣火。 思想解放运动的“闯将”是一批人,而方励之是一个人。思想解放的一批人被剥夺了发言权,能够发言的方励之一个人顶替了一批人。他是孤独的,需要更大的勇气;正因为如此,他一个人的声音涵盖了一个时代。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后,方励之也被撤消职务、开除党籍。有关方面将他的言论编成《方励之谬论汇编》,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小册子发下去以后,人们争相传阅,将反面教材正面读,反而扩大了他的影响。有关方面发觉后要求全部收回,谁知收不回来了,部分小册子已被有心人珍藏。 方励之发出的最强音是民主的呼喊。他有一句名言:“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到上争取的。”这句话改变了中国人关于民主的观念。人们常说“发扬民主”,以为民主是从上面发扬下来的。这是祈求开明专制下的仁政,不是实行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在民的民主。方励之任科大副校长时,与校长管惟炎密切合作,提出大学生应培养“科学、民主、独立、创造”的精神,也是四项基本原则,好像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唱反调。《人民日报》上“民主办学在科大”的栏目不断连载。在他们当校长、副校长期间是没有党委书记的,一时之间,科技大学又成为民主大学,气象万千。 当时方励之有一个著名的口号:“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激励人们去争取民主。直接受他影响的科大学生,成为全国学潮的带头羊。 方励之将民主引向人权,这是他的思想的深刻所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新啟蒙》创刊发布会上,他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人权是民主的核心问题”。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没有为天安门一代的年轻人所理解,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叫做“爱国民主运动”。不仅是他们,从遥远的“五四”以来,中国人往往将民主附丽于爱国,以爱国为最高范畴。人本身是人的最高价值,因而人的一切活动应以人权为最高范畴。民主和爱国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当权者还可以用爱国来压制民主。真正的民主是通向人权,不是通向爱国。以爱国民主运动求民主,是思想上的迷误,也是民主不得实现的症结。今后,中国的有志之士应当发起的是人权民主运动。 历史上的角色定位 方励之首先是科学家。他所受的科学训练,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他的彻底性在于,运用独立思考,特别是宇宙大尺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观察人生。方励之是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科学家并非都有科学精神。对于有些人来说,科学只是谋生的手段,不是人生的态度。一九五八年,有的科学家揣摩上意、迎合风向,为粮食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作论证,就是没有科学精神的表现。方励之继承了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的传统,不为偏见所束缚,不为权势所屈服,一贯坚持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是相通的。追求科学真理和谋取人民利益也是一致的。方励之又是“五四”启蒙先驱的传人,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在八十年代进行新的思想启蒙。 中国从来不缺起义首领、造反好汉、革命英雄、政治领袖,缺的是伏尔泰、狄德罗式的启蒙思想家。方励之以科学家的身份进行思想启蒙,这就是他在历史上的角色定位。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和确定自己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必服从别人的意志。对人物的评价,应当符合他本人的角色定位。许多好意的颂扬和恶意的攻击,大多不符合方励之的角色定位。 一九八九年前,他鼓吹自由和民主,起了动员的作用。有人就称他为“民运领袖”、什么“领导人”、什么“领军人物”等等。中国官方又称他为制造动乱的“黑手”、“后台”等等。这些,都是强加于人的角色错乱。 不符合角色定位的苛求 一九八九年四、五月间,方励之每天都到北京天文台去上班,指导研究生,还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他忙于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插手”运动。他对民主运动是支持的,但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无休止地绝食,以至有的学生领袖声言“期待流血”,都不符合他的理念。他在中国科技大学就曾劝阻学生上街。“六四”邓小平大开杀戒,镇压民主运动,并以方励之为首恶。这是毛泽东、邓小平处理群众闹事的一贯格式,锁定和严惩一两个“黑手”、“后台”,以吓退和驱散众人。方励之当然不能对这场并不完全符合自己的理念、实际上也没有“插手”的运动负责;更没有必要为此结束生命。所以他和李淑娴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一年后,经中美两国谈判,离开中国,转道英国到达美国。二〇〇五年,我们相聚在普林斯顿的林培瑞家。林是陪同方、李进入大使馆的。事后忆当年,方说:“当时不知道邓小平杀人的劲头究竟会疯狂到什么程度,真以为有掉脑袋的危险。要说怕死,也可以,……。”我就说:“应当诅咒的不是怕死,而是为什么要叫人去死?不怕死又怎么样?问题是,当时是否值得你去死。”有人批评方励之,为什么不能像叶利钦那样,登上坦克,振臂一呼?为什么不能像谭嗣同那样,为变法杀身成仁?从主观愿望和客观条件来说,方励之都不可能扮演叶利钦、谭嗣同的角色。这不是方励之的过错,而是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的苛求。 还有人批评方励之躲进美国大使馆是丧失民族气节。按国际惯例,因逃离政治迫害、保护生命而寻求避难是合乎正义的。人类正义高于民族原则,无可责备。在中国,也有先例。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使馆的帮助下,逃出中国。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被段祺瑞政府通缉的李大钊,躲进了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一九四六年,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后,民主人士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躲进了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所以这种批评至少是不了解历史。 角色的转换 方励之是在一定条件下升起的启明星,条件变化了,启明星也将隐退。启明星不是“不落的红太阳”。在美国,方励之的角色转换了。有人批评他,为什么淡出民运?为什么不站出来统合海外各种异议势力?不是淡出,而是本来就不符合他的角色定位,他不能按照别人的意志强迫自己成为政治活动家。还有人问他,为什么他不能以自己的号召力把在北美的各个政党统一起来,像孙 中山一样,组织一个类似当年国民党的海外反对党?方先生本人应该是当然的领袖。他说,当年孙中山的做法,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实际上是恐怖主义活动,包括暗杀、政变、暴动等。方先生希望中国走非暴力的道路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温哥华吴伟) 方励之原来的角色也难以为继了。自由的西方不需要他来启蒙,而专制的中国虽然需要启蒙,但它筑起了“防火墙”,海外人士又无法进行启蒙。方励之恪守本分,成为独立知识分子。科学上,任何命题都有边界条件,越过边界条件,真理就变为谬误。历史上,角色定位,怎样做人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在边界条件以内发挥的正面作用,越过边界条件,可能会成为负面作用。方励之的科学精神用在自己身上就是严格执行做人的边界条件,做应该做、也能够做的事情。不像有些人不知自己做人的边界条件,奢望成为“中国的瓦文萨”、“中国的曼德拉”、“中国的哈维尔”,结果不但毁了自己,也阻挡了真正的“中国的瓦文萨”、“中国的曼德拉”、“中国的哈维尔”的出现。我有时就某些重大事件约他写评论文章。他说,我理论上不行,这种文章写不好。他写的散文,夹叙夹议,相当精彩。他清醒地知道自己什么行、什么不行。 励之,你走得真不是时候。现在,中国的上空彤云密布,暴风雨就要来临,终将冲刷泼在你身上的污水。你等不到这一天了。 一九九三年一月,我到美国不久,与先期到达的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相聚于华盛顿,留下了合影。照片上的四个自由化分子,走了三个,剩我一个,茕茕孓立,黯然神伤。天公青睐,我必长寿。总有一天,我将代表你们,跑到天安门前大喊一声:“自由化分子回来了!”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八日于美国奥马哈
揭秘:朱德孙子因“流氓罪”被枪决始末 2012-05-10 15:29:19 新闻周刊
1974年6月22日,朱德唯一的儿子朱琦(1974年6月10日)刚刚去世12天之后的一家合影。前排左起:康克清、朱德、赵力平;后排为赵力平的5 个孩子,左起:朱国华(五子,1983年9月以“流氓罪”被处决)、朱和平(次子)、朱全华(四子)、朱援朝(长子)、朱新华(三女) 2011年12月1日,是朱德诞辰125周年。 此前,朱德唯一儿子朱琦的夫人、年过八旬的赵力平老人,一直忙于大型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在她位于北京玉泉路一个普通公寓楼的住宅里,她和朱德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袁存建见了面,两位老人高兴得拥抱起来。 赵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大定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44年经组织介绍,在贺龙的撮合下,三张铺板一拼,与朱琦结婚。解放后,赵力平任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组织科科长,1957年任天津中心妇产医院副院长,1979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1988年离休。 赵力平与丈夫朱琦育有四子一女,分别是朱援朝、朱和平、朱全华、朱新华、朱国华。其中,朱新华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而最小的儿子朱国华则在1983年9月“严打”期间,以“流氓罪”被枪决了,死时年仅25岁。 1997年刑法修订,“流氓罪”被删除。很多人为朱国华打抱不平。对此,赵力平女士坦然做了回应。 赵力平身材偏瘦,但精神矍铄,说话娓娓道来,对于唏嘘往事,非常释然,“想得很开”。 朱琦的生母和养母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前夫人尼姆·威尔斯1937年在延安第一次见到爹爹,她说:“我当时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是那样的一个军人,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这在中国更属少见。他无疑地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多情的人。” 的确,爹爹是一位军人,但很重情意。由于烽火战乱,他一生先后有过4位妻子。 我爹爹的原配夫人是肖菊芳,他们是在昆明认识的。肖妈妈的爸爸在昆明有个货栈。爹爹从上海到云南陆军讲武堂考试,步行就得70多天,那个时候爹爹没钱,在路上生病休克了,肖家救了他,爹爹就在肖家养病。 养病期间,爹爹总是每天早起扫院子、挑水,特别勤劳。肖家父母一看,这么好的人呐,爱劳动,还朴实,就把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爹爹,爹爹和肖妈妈就这么在一起了。 他们结婚后生了一个男孩,那就是我的丈夫朱琦。生产之后肖妈妈得了妇女病,数月后病故。朱琦出生时,爹爹发现他右耳际有一根细细的“拴马柱”,于是为他取小名“保柱”。 朱琦还小,爹爹带着不方便,朋友就介绍了四川泸州人陈玉珍与他结婚,陈玉珍是一名比较进步的青年学生,婚后一直带着朱琦。 朱琦很小的时候,陈妈妈就把他带走了,有人说他1917年出生,有人说1919年出生,他自己也说不清。陈妈妈对他就像对自己亲生儿子一样,特别好。爹爹很感激陈妈妈把朱琦养大成人。 朱琦由陈妈妈带到十六七岁,直到1937年,他在泸州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我上泸州去过两次,陈妈妈祖上的房子还在,结婚的床、结婚的东西还在。 康妈妈比爹爹小20多岁,一生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15岁参加革命,17岁上井冈山投奔红军,领导妇女闹革命,泼辣能干。1929年,红四军由赣南进入闽西,占领了闽西重镇长汀,部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 就在休整期间,经过贺子珍和曾志的介绍,爹爹和康妈妈结婚了。尼姆·威尔斯曾写道,在延安采访时,她与朱总司令夫妇和周恩来一起吃饭时,见康克清顽皮地敲着朱德的手臂,而这位红军总司令也微笑地看着自己年轻的妻子,心里好像有说不出的高兴。 拒绝了组织介绍的对象 朱琦被抓壮丁后没有暴露身份,要是暴露了身份就被杀了。后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组织找到了朱琦,1937年底将他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朱琦1938年到了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 毕业后,爹爹把他送到前方去了,让他去打日本鬼子。朱琦打仗当中腿脚负伤了,甲等残废,也不能打仗了,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当队列科的科长。 康妈妈找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长彭绍辉,让他给朱琦找个对象。那时候找对象还得经过组织批准组织调查,还得查三代,后来调查完找到了我。 我1926年出生,老家是河北定县大定村。我父亲赵鸿儒很早就参加了八路军,大哥赵士珍、二哥赵士斌也都参加了革命。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教导员顾玉玲通知我到大队部来一下。我们校部有一队二队,我在二队。当时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谁,队部里头有几个人坐着,有个男同志,当时也没介绍他是谁。人家看我,我没看他。他走了以后,校部说没事,让我回去。 第二天,顾玉玲指导员问我说:“小赵你看那人怎么样?”我说:“上次那人啊?我没看他呢。”指导员告诉我那是谁,说想给我介绍总司令的儿子。我说:“我现在多大呀,18岁,太小了,不行。我们那有风俗,找对象得通过父母,父母不同意还不能结婚。”当时我一直没同意。 后来我问我一个同学,也是好朋友:“你说,指导员给我介绍对象,是总司令的儿子,我跟不跟?”我朋友说:“那么大的官肯定不跟,大官不自由。”朋友们都反对。 几个月以后,组织上把我们调到一起了。我从女生大队调到了七分校校部,分配在队列科当参谋,负责统计工作,归朱琦领导。我工作上向他汇报。天天见面,那时我还是坚决不同意。 有一次,他说:“咱们两个怎么样啊?组织跟你谈了吗?”我说:“谈了,不怎么样。你们家官太大了,我们家是老百姓,不行。”他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其实,我对他的印象还行,比较热情,也挺客气的。 贺龙“逼婚”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迁离延安,转移到晋绥根据地的内蒙古丰镇。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师司令部,他当通讯科科长,我是文书科参谋。 后来贺龙天天动员谈话,他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这是交给他的任务啊。贺龙和甘泗淇将军的夫人李真没事吃了饭就说,小赵出去遛遛吧,遛遛就问我想好了没有。 有一次,贺龙跟我谈话说:“咱们快进张家口了,小赵,你们两个的事定下来,定下来我们就进张家口了,不结也得结,结也得结。同意不同意?什么时候结?”他说:“我是司令员,我说了算,我签字,说结婚你们就算结婚了。”他拍着桌子说:“怎么还没同意,还等什么?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马上结婚!” 说完,贺龙就写了一张条子:“批准朱琦同志与赵力平同志结婚。”边写边说:“这是你同意的,可别说我逼你的,我没逼你。” 条子写好后,交给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结婚证书。 1946年3月23日,我们在丰镇结婚。晋绥军区司令部的人都来参加了,摆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个人。贺龙主持的婚礼。他叼着烟斗眯缝着眼睛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进了张家口,我们照了结婚照,朱琦给他爸爸一张,我送给舅舅一张。解放后,我去找婆婆肖菊芳家的人,发现都没有人了,肖妈妈的亲弟兄、孙子辈都没有了。 大约一年后,1948年8月,我才第一次见到爹爹和康妈妈。西柏坡首长住得也挺简单,都是窄窄的小窗户那种房子。 见面时,爹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军装,待人和蔼,慈祥的脸上总泛着笑容,言谈举止间一点架子也没有。我心里一下踏实了,拘束感也消除了。 康妈妈还笑着说:“你们早点要个孩子吧,爹爹喜欢孩子。”我和朱琦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三天就早夭了,由于怕引起他们伤心,我们没有告诉两位老人。 不久,铁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庄铁路局当工人。因为爹爹说要从头学,已经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先当练习生,后来又当火车司炉,三年后当副司机,又由副司机转为司机,学会了开火车。 孩子们被送进中南海 1949年天津解放,我参与接管了伪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随后成立,我担任组织科科长。1957年,干部支援文教系统,我被调到了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做副院长,一直做了17年。 那时候让你上哪,你从来不会说我不愿去,让你去你就去。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将近50年没动过工作,也不敢要求调动。我想调也不敢说。我爱人在北京,我在天津,这么来回跑,又辛苦。我星期六晚上十点了回北京家里,休一天,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他在铁路,我坐火车不要钱,就这点方便。有时候星期天晚上回来,有时候星期一早上六点坐火车回来。 后来,朱琦调往天津铁路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区。在北京与北戴河间的往返中,火车常常会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铁路局换车头。 一次,朱琦从北戴河开车回到天津,他还未离开机车,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长请你立即到车厢里去一趟。”因为乘车首长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这位首长是何人,来不及收拾,就匆匆赶到会客室。 因为那时开的是蒸汽机车,烧的是煤,朱琦手上、脸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发套都被他坐黑了。这时会客室的门开了,爹爹走了进来。朱琦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长原来是爹爹。 从司炉干起,朱琦一直到“文革”前夕,才当上北京铁路局车辆处的处长。 1950年,我又怀孕了。孩子降生之际,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战役结束,攻占了汉城。于是,爹爹给孙子起名“援朝”。爹爹和康妈妈一再要帮我们带孩子。我只好把10个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此时,双方已开始在三八线附近的开城为停战而谈判,虽然常常是谈谈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爹爹为他取名“和平”。 和平刚8个月,就被送进了中南海。因为两个孩子都在北京,我们的周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过。 爹爹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的兄弟,他参加革命早早离家,养家煳口的担子全落在兄弟们身上,家境困难。爹爹决定尽自己所能,替每个兄弟家供养一个孩子来北京读书。 如此一来,孙子、外孙、侄孙们聚在一起,有十五六人了。再加上爹爹和康妈妈老两口,将近20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饭厅一起吃饭,就得挤满两大桌。 当年,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家生活比较困难,就是爹爹家、刘少奇家和陈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员多,需要接济的亲戚多。中央办公厅曾设法给予补助,但是爹爹从来没有去领过。 当时只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是一级工资,但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他们拿的都是四级工资,也就是400多元。 在那个时候,任何一层的领导人,除了死工资外,就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了。和党政干部相比,军队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帅的工资和各种津贴加在一起约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帅的工资。但他以已经不在军队中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为辞,坚决不拿元帅的工资。 朱琦病逝 朱琦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牵连。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爹爹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爹爹,就拿朱琦撒气,批斗、抄家便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当年年底,他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1972年,才给重新安排了工作。 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也由于“文革”这几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脏病,在家休养。 1974年6月的一个周一,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去了,朱琦和单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我赶回家,他已经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孩子们都不在家,他们都当兵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朱琦走时,只有50多岁。 怕爹爹经受不住这个噩耗,只说“朱琦突然犯病了,在医院抢救”。6月20日,朱琦去世后的第10天,我们回北京去见爹爹,康妈妈才告诉爹爹。 那天,爹爹显得很虚弱。看到爹爹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来到客厅,我忍不住就哭出了声。爹爹看着我,喉结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但一时没有说出声。这时,坐在我旁边的康妈妈,轻轻地拍了拍我,示意别再哭了。爹爹说:“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最小的儿子被执行死刑 我1988年12月底正式办理离休手续。我一个人在天津,身边没有一个子女。我打了个报告,1996年才调到北京。 1983年“严打”期间,天津一天内处决了82人,国华就在里面。国华1957年出生,出事时才25岁。他不是什么天津人民银行的行长,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天津铁路系统工作。与国华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 国华不爱说,不怎么出去,他喜欢画图,制作写字台、单人床,像个“小木匠”。家里也不像人传的那样,地上有地毯,桌上有电视机,都没买。 当时的形势是“严打快打”。当时有人说把责任都推到国华身上,朱国华有他爷爷朱德,肯定不会难为他,国华被推到最前面,结果其余人被放,最年轻的国华被枪毙。 这个事情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有很多不实的传言,比如说:“邓小平找康克清谈话了,做她的思想工作。”“康克清很气愤,说‘这是在朱老总头上动刀子!’”“康克清去天津了解情况,想给孙子减刑。”“朱家的子孙都不是康克清亲生的。她没有感情。” 其实,康妈妈从未介入此事,也没有任何领导人找她谈过话。有人说,康妈妈在饭桌上对着孙子们发火:“你们出了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是在折腾你爷爷!爷爷有话在先,你们如果不争气,做了违法的事,要我登报声明,与你们断绝关系!”这话我也是没听过。 有人说朱国华并没有死。但我并没有见过,没见过也不会相信。别人说,时候不到,时候到了会团圆的。我已经听到不止一人说朱国华未死。30年已去,死不死无所谓了。
罗纳德里根演讲《邪恶帝国》节选
标题:网友推荐:罗纳德.里根演讲《邪恶帝国》节选,中英对照背诵后四级一次考过,^^. 由此我将谈及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在我作为总统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一个直率的问题时,我曾指出:苏联领导人是不错的马列主义者,他们开诚布公地宣称,他们所承认的唯一道德就是推动他们的事业,就是世界革命。我想我应该指出,这里我只引用了他们的精神导师列宁的话,他在1920年曾说,他们摒弃一切源于超自然观念的道德——那是他们给宗教下的定义——或与阶级学说无关的观念。道德完全服务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一种东西是否道德,取决于它是否为消灭旧的、剥削性的社会秩序和统一无产阶级的事业所必需。 是的,我想许多有影响的人士拒绝接受苏联教条的这一基本观点体现了对于极权主义本质的历史性抗拒。我们在30年代就目睹了这种抗拒。今天我们依然到处可见这种抗拒。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自我孤立并且拒绝寻求与他们的谅解。我打算尽一切努力去使他们相信我们的和平意愿,我要提醒他们,是西方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拒绝利用其在核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以扩张领土,同样是西方在今天提议削减50%的战略弹道导弹,以及销毁全部的陆基中程核导弹。 但是同时,他们也必须明白,我们永远不会拿我们的原则和准则讨价还价。我们永远不会出让我们的自由。我们永远不会背弃对上帝的信仰。我们也永远不会停止谋求一种真正的和平。但我们不能保证美国所支持的这些东西能够通过某些人士提出的所谓核冻结方案得到维护。 真实情况却是,现在的冻结将会成为一种非常危险的欺诈,因为它仅仅是和平的幻象。实际上我们必须通过实力来寻求和平。 只有当我们能够冻结苏联的全球野心时,我才会同意某种冻结。在当前水平的武器冻结将使苏联在日内瓦与我们进行认真谈判的动机不复存在,事实上它会断送我们提出的削减主要军备的机会。更有甚者,他们会通过冻结来达成他们的目的。 一次冻结给予苏联的奖赏就是它庞大而且无与伦比的军事积累。却会阻止美国及盟国的国防现代化,使我们日趋老化的军事力量弱不禁风。一种诚实的冻结会就限制的系统和数量、确保有效性核查和执行的措施等问题进行广泛的先行谈判。而现在提出的冻结实际上不可能进行核查。这样一种努力会使我们完全偏离目前进行的达成实质性削减的谈判。 几年前,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人数众多的集会上听到一位年轻人的演讲。他是位年轻的父亲并且在娱乐圈名声大噪。在冷战期间,共产主义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为许多人萦绕心头的一个问题。当时他所谈的就是这个题目。突然,我听到他说:“我爱我的女儿们甚过一切。”我自言自语道:“哦,别那么说。你不能那么说,别说那个。”但是我低估了他。他接着说道:“但我宁可看到我的孩子们现在怀着对上帝的信念阖然长逝,也不愿她们在共产主义的阴影下成长,并且有朝一日带着对上帝无所信仰的心态死去。” 听众当中也有好几千年轻人。他们站起身来,欢呼雀跃。他们立即就明白了他的话中所包含的深刻真理,即物质与精神何者是真正重要的。 是的,让我们为所有那些生活于极权主义黑幕中的人祈祷。祝愿他们发现认识上帝的喜乐。但是在他们认识上帝之前,我们必须警觉,只要他们继续鼓吹国家的至高无上、宣扬国家对于个体的万能、并预言它将最终统治全人类,他们就是现代世界的邪恶中心。 鲁益师在他令人难忘的《地狱来鸿》中写道:当今最大的邪恶并非是在狄更斯所热衷描绘的、肮脏的“罪恶之窟”中炮制出来的,它甚至不是在集中营和劳改营犯下的,那些地方只是邪恶发作的最终结果。当今最大的邪恶是在整洁豪华、温暖明亮的办公室里构思和安排的;是由那些衣着光鲜、言谈斯文的人鼓动、支持、散布和记录的。 结果,由于这些人言谈斯文、由于他们有时流利自如地畅谈手足之情与和平、由于他们能象某些以前的独裁者一样总是在“最后才提出领土要求”,一些人就会要求我们相信他们的表白并且顺从他们的非份之想。但是,如果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对对手一味妥协或一厢情愿实属愚不可及。它意味着背叛我们的过去、虚掷我们的自由。 因此,我敦促你们大声反对那些将美国置于军事和道德劣等地位的人士。我一直相信你们这些教会人士才是鲁益师书中那个老魔鬼的眼中钉。因此,在你们讨论核冻结提议时,我要提醒你们谨防傲慢的诱惑,那是一种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凌驾于一切之上、并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诱惑。它无视一个邪恶帝国的历史和勃勃野心,径自宣布军备竞赛不过是一场巨大的误会,由此而使自己游离于对与错、善与恶之外。 本届政府在尽力使美国保持强大和自由,当我们正在为真正和可靠地削减核武库、并在上帝的帮助下最终彻底消灭核武器而进行谈判时,有些人会使你们撤回对我们努力的支持,我请求你们抵制这种诱惑。 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是重要的,但我在这里要补充一点:我始终确信,当前为世界而进行的抗争从来不取决于炸弹或火箭,也不取决于军队或军事力量。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真正危机是精神上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对道德意志和信仰的检验。 惠特克•钱伯斯——这位希斯-钱伯斯间谍案中的主角、这位以其自身的变节而见证了我们时代可怕创伤的人——曾写道,某种程度上,西方世界的危机在于它对上帝漠不关心,从而配合了共产主义将人与神疏离开来的尝试。他又说道,马列主义实际上是人类第二种最为古老的信仰,第一种信仰则是伊甸园中的诱惑之音:“你们会像神一样。” 他写道:西方能够回应这种挑战,“但这只有假定西方对上帝及天赋自由的信念与共产主义对人的信念一样伟大才行。” 我相信我们能够迎接这种挑战。我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悲惨而诡异的篇章——即使这一章已经临近终结。我相信这个是因为我们探求自由的力量源泉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而且由于它是无尽的,所以它必然对那些奴役同类的人形成威慑并最终战胜他们。因为以赛亚书这样写道:“疲乏的,他赐气力;无力的,他加力量。但那些仰望主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决不困倦。” 是的,改变你们的世界。我们的国父之一潘恩曾说:“我们拥有重塑世界的内在力量。”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让我们协力同心来完成这项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的事业。 愿上帝保佑你们,谢谢大家。 And this brings me to my final point today. During my first press conference as president, in answer to a direct question, I pointed out that, as good Marxist-Leninists, the Soviet leaders have openly and publicly declared that the only morality they recognize is that which will further their cause, which is world revolution. I think I should point out I was only quoting Lenin, their guiding spirit, who said in 1920 that they repudiate all morality that proceeds from supernatural ideas–that’s their name for religion–or ideas that are outside class conceptions. Morality is entirely subordinate to the interests of class war. And everything is moral that is necessary for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old exploiting social order and for uniting the proletariat. Well, I think the refusal of many influential people to accept this elementary fact of Soviet doctrine illustrates an historical reluctance to see totalitarian powers for what they are. We saw this phenomenon in the 1930s. We see it too often today. This doesn’t mean we should isolate ourselves and refuse to seek an understanding with them. I intend to do everything I can to persuade them of our peaceful intent, to remind them that it was the West that refused to use its nuclear monopoly in the forties and fifties for territorial gain and which now pr-proposes 50 percent cut in strategic ballistic missiles and the elimination of an entire class of land-based,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missiles. [Applaus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y must be made to understand: we will never compromise our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We will never give away our freedom. We will never abandon our belief in God. [Long Applause] And we will never stop searching for a genuine peace, but we can assure none of these things America stands for through the so-called nuclear freeze solutions proposed by some. The truth is that a freeze now would be a very dangerous fraud, for that is merely the illusion of peace. The reality is that we must find peace through strength. [Applause] I would a-[Applause continuing]…I would agree to a freeze if only we could freeze the Soviets’ global desires. [Laughter, Applause] A freeze at current levels of weapons would remove any incentive for the Soviets to negotiate seriously in Geneva and virtually end our chances to achieve the major arms reductions which we have proposed. Instead, they would achieve their objectives through the freeze. A freeze would reward the Soviet Union for its enormous and unparalleled military buildup. It would prevent the essential and long overdue modernization of United States and allied defenses and would leave our aging forces increasingly vulnerable. And an honest freeze would require extensive prior negotiations on the systems and numbers to be limited and on the measures to ensure effective verification and compliance. And the kind of a freeze that has been suggested would be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verify. Such a major effort would divert us completely from our current negotiations on achieving substantial reductions. [Applause] I, a number of years ago, I heard a young father, a very prominent young man in the entertainment world, addressing a tremendous gathering in California. It was during the time of the cold war, and communism and our own way of life were very much on people’s minds. And he was speaking to that subject. And suddenly, though, I heard him saying, “I love my little girls more than anything–” And I said to myself, “Oh, no, don’t. You can’t — don’t say that.” But I had underestimated him. He went on: “I would rather see my little girls die now; still believing in God, than have them grow up under communism and one day die no longer believing in God.” [Applause] There were…There were thousands of young people in that audience. They came to their feet with shouts of joy. They had instantly recognized the profound truth in what he had said, with regard to the physical and the soul and what was truly important. Yes, let us pray for the salvation of all of those who live in that totalitarian darkness–pray they will discover the joy of knowing God. But until they do, let us be aware that while they preach the supremacy of the State, declare its omnipotence over individual man, and predict its eventual domination of all peoples on the earth, they are the focus of evil in the modern world. It was C.S. Lewis who, in his unforgettable “Screwtape Letters,” wrote: “The greatest evil is not done now…in those sordid ‘dens of crime’ that Dickens loved to paint. It is…not even done in concentration camps and labor camps. In those we see its final result, but it is conceived and ordered; moved, seconded, carried and minuted in clear, carpeted, warmed, and well-lighted offices, by quiet men with white collars and cut fingernails and smooth-shaven cheeks who do not need to raise their voice.” Well, because these “quiet men” do not “raise their voices,” because they sometimes speak in soothing tones of brotherhood and peace, because, like other dictators before them, they’re always making “their final territorial demand,” some would have us accept them at their word and accommodate ourselves to their aggressive impulses. But if history teaches anything, it teaches that simpleminded appeasement or wishful thinking about our adversaries is folly. It means the betrayal of our past, the squandering of our freedom. So, I urge you to speak out against those who would place the United States in a position of military and moral inferiority. You know,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old Screwtape reserved his best efforts for those of you in the Church. So, in your discussions of the nuclear freeze proposals, I urge you to beware the temptation of pride–the temptation of blithely..uh..declaring yourselves above it all and label both sides equally at fault, to ignore the facts of history and the aggressive impulses of an evil empire, to simply call the arms race a giant misunderstanding and thereby remove yourself from the struggl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and good and evil. I ask you to resist the attempts of those who would have you withhold your support for our efforts, this administration’s efforts, to keep America strong and free, while we negotiate–real and verifiable reductions in the world’s nuclear arsenals and one day, with God’s help, their total elimination. [Applause] While America’s military strength is important, let me add here that I’ve always maintained that the struggle now going on for the world will never be decided by bombs or rockets, by armies or military might. The real crisis we face today is a spiritual one; at root, it is a test of moral will and faith. Whittaker Chambers, the man whose own religious conversion made him a witness to one of the terrible traumas of our time, the Hiss-Chambers case, wrote that the crisis of the Western world exists to the degree in which the West is indifferent to God, the degree to which it collaborates in communism’s attempt to make man stand alone without God. And then he said, for Marxism-Leninism is actually the second-oldest faith, first proclaimed in the Garden of Eden with the words of temptation, “Ye shall be as gods.” The Western world can answer this challenge, he wrote, “but only provided that its faith in God and the freedom He enjoins is as great as communism’s faith in Man.” I believe we shall rise to the challenge. I believe that communism is another sad, bizarre chapter in human history whose last–last pages even now are being written. I believe this because the source of our strength in the quest for human freedom is not material, but spiritual. And because it knows no limitation, it must terrify and ultimately triumph over those who would enslave their fellow man. For in the words of Isaiah: “He giveth power to the faint; and to them that have no…might He increased strength. But they that wait upon the Lord sha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ey shall mount up with wings as eagles; they shall run, and not be weary.” [Applause] Yes, change your world. One of our founding fathers, Thomas Paine, said, “We have it within our power to begin the world over again.” We can do it, doing together what no one church could do by itself. God bless you,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Long Appla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