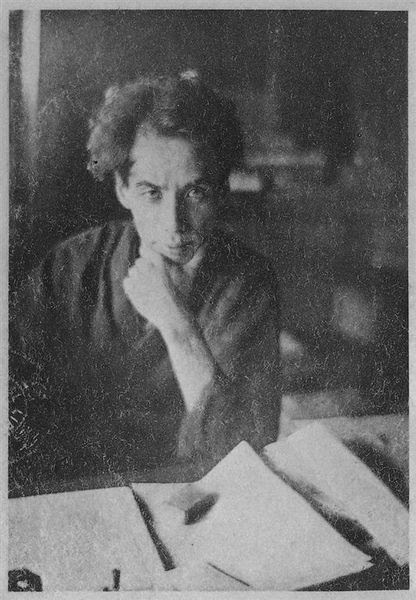如何战胜伊斯兰国
要战胜伊斯兰圣战者,我们需要孤立他们、削弱他们对穆斯林的号召力, 并避免一场“文明的冲突”的发生。
作者:Maajid Nawaz(英国)
伊斯兰教(Islam)是一种宗教信仰,就像其他任何宗教信仰一样,它的内部也很多样化。与之相反,伊斯兰教主义(Islamism)则是把单一版本的伊斯兰教强加给全社会的欲望。伊斯兰教主义不是伊斯兰教,但它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分支,它是穆斯林神权政治。
与此相仿,圣战(jihad)是一种传统的寓意抗争的穆斯林观念,有时是个人精神信仰的挣扎,有时是抗击外敌的斗争。然而,圣战主义(jihadism)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是借用武力强行传播伊斯兰教主义。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许多自由派思想的左翼评论家一直对于如何称呼伊斯兰思想体系谨小慎微。他们似乎担心穆斯林社群和宗教排异者们听到“伊斯兰”这个词,都会简单地把极少数圣战主义者的过激行为归罪到全体穆斯林头上。
我把这种状况称为“伏地魔效应”,取自J?罗琳《哈利·波特》小说中的那个魔头。罗琳女士小说中许多善良的人物被伏地魔的邪恶吓坏了,以致于他们要么根本不敢直呼“伏地魔”的名字而是用“那个谁”指代,要么干脆直接阿Q般地否认他的存在。然而这种恐惧只是加剧了人们歇斯底里的恐慌,从而进一步放大了伏地魔的邪恶力量。
同样的对于伊斯兰教歇斯底里的恐慌也正逐渐展现在我们眼前。然而,如果连对伊斯兰教主义和圣战主义的暴力展示方式都不敢直接表述、单独提及和充分理解,那么,任何想要挫败伊斯兰教主义的战略都根本不会成功。我们当然不能把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教简单等同起来,然而说两者毫无瓜葛也实在不太可信。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教既不是处处相关,也不是毫不相干,而是的的确确有“一些”关联。这里的“一些”就是那些伊斯兰教主义者援引伊斯兰教经文捍卫他们的观点、并在穆斯林中招兵买马的内容。
厘清上述提及的这些概念的紧迫性,对每个人来说都显而易见。我们已经看到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伊斯坦布尔、西奈半岛、贝鲁特、巴黎、圣贝纳迪诺、伦敦。这些伊斯兰国思维的暴力背后是什么的战略呢?所有圣战分子都在寻求制造事端。在西方,他们激化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在东方,则是推动逊尼派穆斯林反对什叶派穆斯林。伊斯兰教主义神权政治意识形态着力渲染三个方面:分裂主义,极端对立和穆斯林的受害者地位。
伊斯兰国的头目坚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在挑起同整个伊斯兰和穆斯林世界的全球战争。这显然是无稽之谈。然而,通过挑衅和一点点自圆其说的预言这两个手段相结合,伊斯兰国正在尽一切可能使之成为现实。这其中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不久前“把穆斯林彻底全面拒之于美国大门之外”的号召也助了一臂之力。伊斯兰国的目标是要让逊尼派穆斯林难民在欧洲、美国和中东地区再也无处藏身避难,而只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非法恐怖组织区域、也即他们自封的哈里发王国里生存。
正如伊斯兰国在自己的官方杂志《Dabiq》中所描述的那样,它的目的是消除处在伊斯兰教主义神权政治和反穆斯林偏执狂之间的所谓中间“灰色地带”,从而让每个人都得被迫选边站队。伊斯兰国希望以这种方式将非穆斯林推向反穆斯林的境地,而这个过程一旦完成,也就是说,一旦大家都开始用狭隘的宗教视角看待彼此的时候,伊斯兰国就将掀起世界宗教战争。
我本人也感觉到肩负个体责任,就是也要努力消除灰色地带、促使穆斯林在西方世界失去家园。作为一个年轻的在英国长大的穆斯林,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伊斯兰教组织的领导者之一,我花了超过十年的时间,致力于复兴哈里发王国。尽管并非通过恐怖主义途径,但我的这些工作最终导致了我在24岁的时候被关进了埃及专门关押政治犯的Mazra Tora监狱,并在那里蹲了5年。
后来在“大赦国际”组织的努力帮助下,我在监狱里得以重新思考和评估我的所有思想。接下来的五年里,我一点点使得自己“去极端化”。最终,我意识到,我所信仰的伊斯兰教,正在被极权政治所利用,必须从神权政治的笼罩下重新解脱出来。在后来的八年时间里,这也正是我创立了一个反极端主义组织所致力于推动的唯一目标。
这种抗争可能胜利,但绝不会容易。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系列的调查发现,英国人的态度反映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根据二月份ComRes为BBC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民显示,25%的英国穆斯林同情巴黎查理周刊枪击案的作案者。2008年的一项YouGov的调查发现,穆斯林学生中有三分之一相信,为了宗教而动手杀人是合理的,而40%的人希望英国接纳伊斯兰教法(Shariah)作为法律。另一份在2007年由Populus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英国年轻穆斯林中36%认为叛教者应该受到“处死的惩罚”。
那接下来的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有多达1000名英国穆斯林加入了伊斯兰国,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参加英国陆军预备役的人数。
伊斯兰国武装的真正实力可能介于中央情报局估计的3万2000人与库尔德族人估计的20万人之间。依据总部位于纽约的一家私人情报公司Soufan公司的数据,涌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和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外国人数量在过去18个月中翻了一番,可能高达3万1000人。
最新的一项针对11个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的调查显示了公众对于伊斯兰国的广泛反感,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令人担忧的不少支持。只有28%的巴基斯坦人不拥护伊斯兰国,而62%表示没感觉。在尼日利亚,14%的受访者对伊斯兰国有好感;在马来西亚和塞内加尔,好感率是11%;在土耳其,8%;在巴勒斯坦,6%。综上所述,尽管全球16亿穆斯林并没表现出大多数的支持,但这些数字仍足以令人担忧。
巴黎袭击后,罗马教皇表示我们正处于微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更准确的说,我们面对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来自圣战主义者的暴动。伊斯兰国正是这一暴动的最新化身。穆斯林国家的政府有诸多的不足之处,由此便为伊斯兰教主义者们的社会运动留下了空白。伊斯兰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酝酿了几十年而横空出世的。把伊斯兰国定性为暴乱活动至关重要,越南战争的教训表明击败暴乱和赢得一场常规战争完全不同。
要平定暴乱必须明确,敌人在其招兵买马的社群里拥有极大的民意支持。反暴乱的战略目的应该是挫败能够帮助敌人进一步招募新人的宣传成果。必须把暴乱分子从他们的目标招募社群之中隔离孤立出来。这需要心理战、实体战和经济战的综合运用,目的在于瓦解暴乱分子的意识形态、组织运营和收入来源。
这一战略最为至关重要的部分是信息发布。抗击伊斯兰国,我们必须避免使用那些宣传它世界观的语言,同时提供更具震撼力的另一套替代语言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抵御伊斯兰教主义者和圣战主义者们吸引煽动穆斯林听众的能力。
在这一努力进程中,拒绝承认伊斯兰极端主义这一现实问题的存在的穆斯林们,其实和特朗普先生以及其制造贩售恐慌论调的民粹主义支持者们同样具有适得其反的作用。双方都起到了加剧宗教撕裂分化和不信任的作用,而极端分子对此甘之如饴。伊斯兰国就是以挑起“文明的冲突”为己任的,我们当然不应该助他们一臂之力。
这些失语和缺位会带来什么代价?如果没有一套语言能够准确分辨伊斯兰教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和广大非伊斯兰教主义的普通穆斯林之间的差异,西方那些充满焦虑担忧的非穆斯林人群就可能轻易地被夸张的媒体报道和渴望吸引眼球的的政客所误导。于是有些人就会简单粗暴地认为,所有问题都怪伊斯兰教本身和全体穆斯林。这就是为什么仇外政治近来在欧洲和美国得以崛起的原因所在。
至于穆斯林社群本身,如果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主义和伊斯兰教压根儿无关,那也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了。因为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这样的彻底否认的立场妨害了那些勇敢的伊斯兰教改革的宗教研究家们的努力,比如英国的乌萨马·本·哈桑、巴基斯坦贾韦德·艾哈迈德·???m???和美国的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安??'?m,他们都在迫切尝试建构反伊斯兰教主义、促进改善言论自由、性别平等等基础人权的宗教理论基础,由此抵御和对抗那些极端暴乱分子们所发布的理论和信息。
彻底否定的立场同时也背离了许多被围攻的前穆斯林的声音,如巴基斯坦裔的加拿大作家阿里?.里兹维,他为了那些平等基本人权能够在自己所在的穆斯林社群中得到承认而抗争。这些改革者们都需要一套语言体系,让人们能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极端分子圣战分子们所兜售的扭曲政治状况严格区分开。
正如一个人并不一定非得是黑人才能反对种族主义,不一定是同性恋者才能关心同性恋平权,人们也不必非得是穆斯林才能公开反对穆斯林神权政治。考虑到美国的建国历史,美国人最具有优势来解释为什么神权政治对人类文明从来没有好处。他们也可以帮助欧洲人应对后移民时期建立身份认同的挑战。
我的许多穆斯林同胞反对兜头直击批判极端伊斯兰教主义。他们的想法是“为什么我们要为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事情道歉”。但是,正如我们穆斯林期待其他族群的人们能够团结一致批驳诸如特朗普先生这样常出奇谈怪论的反伊斯兰的偏执傲慢者一样,我们也有责任团结起来公开反对极端伊斯兰教主义。
有一个反暴乱战略对外交政策的实际进行有什么意义?总统乔治·W·布什大概会轻率侵占伊拉克从而掉入圣战分子的泥潭,而奥巴马和国际社会则正在向叙利亚这另一悬崖绝壁上梦游靠近。诚然,干预叙利亚局势会被伊斯兰国借以当做进一步招兵买马的口实,然而我不干预则已被他们当作证据来表明,国际社会抛弃了叙利亚人,扔下他们孤独无依地面对巴沙尔·阿萨德的炸药桶。
当初我自己加入激进组织的旅程并不是始于国际社会对地区冲突的干预,反而是国际社会未能对波斯尼亚种族灭绝进行干预。我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但是不作为和正面入侵一样危险。只要伊斯兰教主义者依然控制对年轻的易怒的穆斯林们的宣传舆论,无论我们的行动还是我们的不作为都可以成为煽动他们极端化的理由。
世界正面临全球范围内的圣战主义者暴乱,这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行动,以伊斯兰教主义意识形态为精神支撑,始终对一些穆斯林极具号召力和诱惑力。经过巴黎和圣贝纳迪诺之后,奥巴马政府抗击伊斯兰国的政策正在瓦解失效。从去年一月把伊斯兰国形容成“散兵游勇”,到巴黎系列恐袭之前声称伊斯兰国已被遏制,奥巴马先生的步伐总是比伊斯兰国的发展慢上半拍。
我们反暴乱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应不再让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只是敲边鼓。是的,这可能会使得我们的土耳其盟友感到不舒服,也会让伊拉克的统治者感觉棘手。然而别忘了,库尔德人已经一遍又一遍证明了在和伊斯兰国的对抗中他们是唯一卓有成效的战斗力量。
如果这意味着将出现一个库尔德国家,那又如何!除了在北非的突尼斯正在进行的持续实验之外,一个新的库尔德国家可能会成为中东唯一的世俗穆斯林民主国家。它将可能成为中东地区的政治和宗教的灯塔。然而我们的外交政策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在忽略这种可能性,这是难以原谅的。
针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还必须有国际地面部队的配合支持,数量不必太多,几千人即可,应由逊尼派阿拉伯人充当前锋,特种部队和支持人员但应后应。所有军事力量齐心合力着力把伊斯兰国从其摩苏尔和拉卡的据点清除出去。至于阿萨德先生,作为与俄罗斯和伊朗保持关系的妥协,叙利亚政权应继续保持,但阿萨德先生必须下台。
这样的行动一定会削弱伊斯兰国的日常运作能力,但不会挫败它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号召力。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最先“启蒙”了基地组织,现在又“启蒙”了伊斯兰国,将来还一定会继续“启蒙”其他人。伊斯兰国成功洗脑了大约6000名欧洲人加入他们行列,而能做到这种极端化的可不只有他们,说服灌输招募他人可不是空穴来风。伊斯兰国的洗脑很厉害,但还不至于厉害到没朋友。
事实上,伊斯兰教主义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宣传洗脑早已成功催芽这些欧洲年轻穆斯林对于神权政治的向往。我上面提到的youGov的调查发现,有33%的年轻英国穆斯林表示希望看到一个全球性的哈里发的复兴。在欧洲努力已久的其他伊斯兰主义者组织早已埋下种子,伊斯兰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摘了桃子。
扭转这一局面将需要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几十年的共同努力,而要最终取胜则必须是能够使得极端伊斯兰教主义意识形态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无论认知层面还是社会层面。
(作者纳瓦兹先生是总部位于伦敦的反极端主义组织Quilliam的主席,著有《激进:走出伊斯兰教极端主义之旅》。)